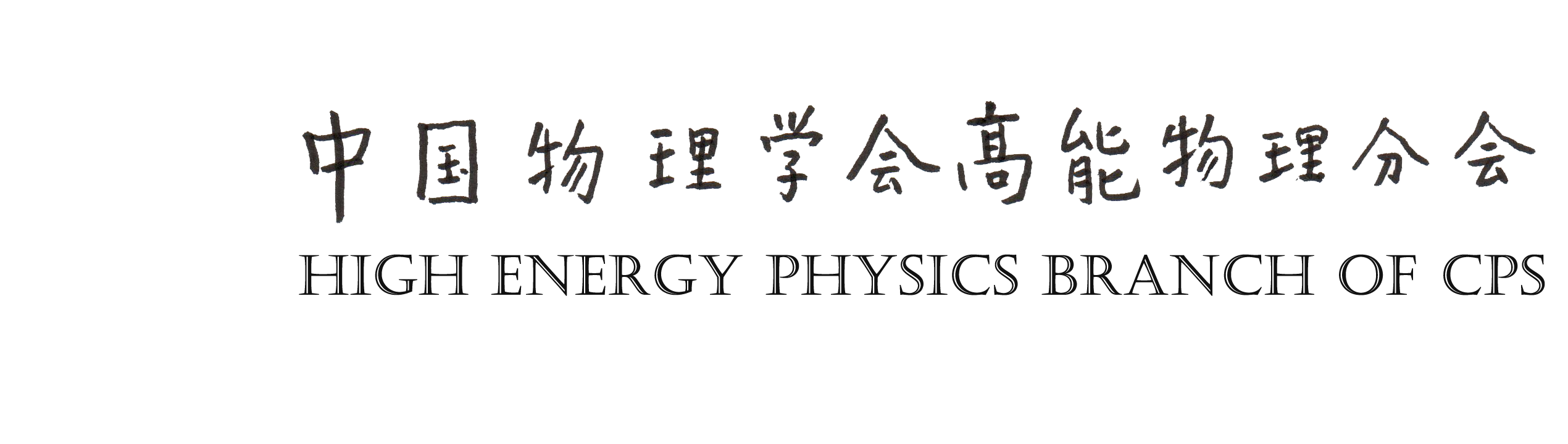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建立于20世纪60~70年代,它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经受住了无数次科学实验的检验,成为人类描述和理解各种强、弱和电磁相互作用现象最成功的理论工具。但是该模型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它刻意回避了中微子质量及其起源的问题,也无法解答为什么可观测宇宙中不存在原初反物质但却存在大量暗物质的问题。在宇宙大爆炸之初所产生的反物质何以随着宇宙的膨胀和冷却而神秘地消失,以及其背后的动力学是否与中微子的质量起源机制存在某种关联,这是当今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界普遍关心并深入探索的重大课题。理论研究表明,解释中微子质量起源之谜的“跷跷板”(seesaw)机制[1]与解释宇宙原初反物质消失之谜的轻子生成(leptogenesis)机制[2],可能是问题背后的答案。而连接这两个机制的桥梁就是超重的“惰性”马约拉纳(Majorana)中微子[3]:它们在宇宙早期神秘地产生,与已知的“活性”中微子通过极其微弱的汤川(Yukawa)相互作用建立关联;它们的衰变则导致了宇宙的轻子与反轻子不对称,后者部分转化成宇宙的重子与反重子不对称,而数量占优势、最终存活下来的原初重子形成了今天的可观测宇宙。
1 宇宙的物质与反物质不对称
为什么包括地球、月亮、太阳、银河系以及人类自身的世间万物都是由物质而不是反物质构成的?为什么天文学家在宇宙空间中始终没有观测到原初反物质?诸如此类的问题在1933年以前几乎无人关注,原因在于那时物理学家所知道的基本粒子仅限于电子、质子和中子,而它们的反粒子¾¾正电子、反质子和反中子还没有被发现。
反物质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理论物理学家狄拉克(Paul Dirac)[4]于1928年提出来的。他建立了描述电子的相对论性运动方程,并由此预言了电子对应的反物质¾¾正电子的存在。后者于1932年被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Carl Anderson)[5]在宇宙线实验中发现了。在193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上,狄拉克对物质与反物质之间的对称性做了精彩的表述。他推测,“如果我们在研究自然界的基本物理规律时接受粒子与反粒子完全对称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必须认定地球上乃至整个太阳系主要包含电子和质子的事实纯属偶然。很有可能在一些其它的星球上情况正好相反,即这些星球主要是由正电子和反质子构成的。实际情况也许是,半数的星球由物质组成,而另外半数的星球由反物质组成。这两类星球的光谱完全相同,目前的天文观测手段无法区分它们[6]。”狄拉克这番话代表了一种新宇宙观的诞生:整个宇宙包含等量的物质与反物质,而两者之间是严格对称的。换句话说,可能存在一个与我们的世界呈镜像对称的世界,那里的一切都是由反物质构成的(图1)。

图1 宇宙大爆炸之初,物质与反物质等量产生的示意图
但是,后来的天文学观测并不支持狄拉克的推断。探测宇宙中的反物质一般有两种途径。首先,如果存在反物质组成的星球,我们应该能够在宇宙线中观测到来自这类星球的反质子和反原子核。然而,科学家从未在宇宙线中发现反原子核。虽然在宇宙线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正电子、反质子和反中子,但这些反粒子实际上是通过质子或原子核与星系气体以及地球大气层相碰撞而产生的,它们的数量与考虑了具体天体环境的理论计算相符合,因此不属于“原初”反物质。其次,在物质与反物质相接的区域,质子和反质子的湮灭反应一定会发生,从而产生若干带电及中性的介子。这些介子最终衰变成光子、电子、正电子、中微子和反中微子。其中光子的谱线很特别,其能量应在140 MeV附近取最大值。可是,天文学观测并没有发现这种特殊的光子能谱。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半径大约为100亿光年的可观测宇宙中几乎不存在“原初”反重子,即其整体上并没有呈现出重子与反重子之间的对称性。
这一结论似乎与大爆炸宇宙学的预言相矛盾。依照大爆炸理论,在宇宙诞生之初,最自然的情形是粒子和反粒子等量地产生,因此重子和反重子的数密度也应该相等,即。事实上,即便宇宙的初始重子数和反重子数不相等,这一原初不对称度也会由于宇宙的瞬间暴胀所导致的巨大稀释效应而变得可以忽略不计,这无法解释基于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各向异性和大爆炸核合成所产生的轻核丰度的观测结果所得到的重子数密度与背景光子数密度之比。故而可观测宇宙的重子生成(Baryogenesis)问题,即从原初的到如今的但的演化,需要一个合理的动力学答案。
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7]在1967年指出,宇宙的重子生成动力学需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1)存在破坏重子数守恒的相互作用;(2)存在破坏电荷共轭变换(C)不变性和破坏电荷共轭与空间反演联合变换(CP)对称性的相互作用;(3)偏离热平衡。在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框架内,这三个条件原则上都可以满足。首先,非微扰的量子反常效应会破坏重子数守恒。在有限温度 GeV范围内,这种量子反常过程处于热平衡状态[8]。其次,弱相互作用破坏C和CP对称性。第三,偏离热平衡的条件可以由电弱相变提供。尽管如此,基于标准模型的电弱重子生成机制所预言的重子与反重子不对称度却太小而不足以解释上述观测结果。而基于大统一模型或超对称模型的重子生成机制由于始终缺乏与这两个理论框架相关的实验证据,也受到质疑。相比之下,与中微子质量起源的“跷跷板”机制密切相关的轻子生成机制,则为解释宇宙的原初反物质消失之谜提供了一条在理论上也许更加令人信服的途径。
2“跷跷板”与轻子生成机制
自1998年以来,在与大气、太阳、反应堆和加速器相关的中微子实验中都观测到了神奇的中微子振荡现象[9]。后者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中微子具有微小的质量且不同轻子味之间存在显著的混合效应,因此在某一源处,通过带电流弱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类型的中微子在空间传播适当的距离后,会由于量子相干效应在探测器处转化成其他类型的中微子。既然如此,如何修改和扩充标准模型使之得以产生中微子质量和轻子味混合效应呢?
在不放弃标准模型的规范对称性、洛仑兹( Lorentz)不变性和可重正化性等量子场论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引入右手征的中微子场是赋予中微子以质量的最简洁途径(图2)。尽管利用左手征和右手征的中微子场以及希格斯(Higgs)场可构建出人们熟悉的狄拉克(Dirac)质量项,但如此这般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微子的质量远远小于如出一辙的电子的质量。不仅如此,右手征的中微子场是群的单态,因此这样的场及其电荷共轭场(后者其实具有左手征)原则上可以构成一个不破坏规范对称性但破坏轻子数守恒的马约拉纳质量项。后者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除非将轻子数守恒作为一个可施加的强制性约束条件。当把上述狄拉克质量项和马约拉纳质量项合二为一,并要求后者的质量标度远远高于电弱对称性自发破缺的能标时,便可以推导出相关轻和重的中微子的质量本征态¾¾它们都满足马约拉纳费米子场的条件,即反粒子场等于其自身。这一通过引入相对于电弱能标而言特别重的自由度来产生并压低已知的活性中微子的质量的思想,就是著名的“跷跷板”机制。之所以称之为“跷跷板”机制,是因为电弱能标充当了支点的作用,而重自由度将跷跷板的一端压下去,翘起来的另一端自然代表由此产生了微小质量的轻自由度,即众所周知的活性中微子。

图2 对标准模型的最小扩充示意图:对应三种已知的活性中微子场,引入三种惰性中微子场,并容许两者之间发生汤川相互作用以及轻子数不守恒效应
虽然“跷跷板”机制只能定性地解释为什么已知的三种活性中微子可以获得微小的质量,但却不能定量地预言相关质量的具体数值。尽管如此,该机制还是受到众多理论物理学家的追捧。原因其实很简单:假设质量足够大的马约拉纳中微子产生于宇宙早期,它们可以通过汤川相互作用发生轻子数不守恒和CP对称性破坏的衰变,转化成轻子或反轻子以及希格斯粒子,从而造成宇宙的轻子数密度与反轻子数密度之间的不对称;后者借助电弱反常过程部分转化为宇宙的重子数与反重子数之间的不对称(由于重子数与轻子数之差在反常的电弱相互作用过程中仍保持守恒,因此轻子生成之初但的状态随着宇宙的演化和的变化会转化成的状态[10]),其中重子的数密度大于反重子的数密度,即差不多每10亿个反重子对应10亿加1个重子;随着宇宙的膨胀和冷却,重子与反重子不断发生湮灭,最终存活下来的重子数密度与光子数密度的比值若满足观测值,就能够解释可观测宇宙的重子与反重子不对称现象,即回答为什么我们今天生活在主要以重子构成的物质世界而不是主要以反重子构成的反物质世界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基本问题。这一利用中微子质量起源的“跷跷板”机制来达到早期宇宙的轻子生成的目的,即“一石二鸟”,从而实现宇宙的重子生成的物理机制,是由日本理论物理学家福来正孝(Masataka Fukujita)和柳田勉(Tsutomu Yanagida)[2]在1986年提出来的。随着中微子物理学实验研究在最近20余年的蓬勃发展,轻子生成机制的理论细节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11]。重的惰性中微子在宇宙早期的产生和湮灭似乎可以与恐龙在地球上的出现和消失相类比。距今大约2亿3千万年前,作为庞然大物的恐龙出现在地球上,它们在距今大约6500万年前神秘地消失,只留下可供人类研究和想象的化石。倘若质量巨大的马约拉纳中微子也曾短暂地存在于宇宙早期,然后神秘地衰变,使得导致活性中微子获得质量的“跷跷板”机制与导致原初反物质消失的轻子生成机制都起作用,那么它们留给我们可供发掘的“化石”有哪些呢?
3 如何检验“一石二鸟”图像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跷跷板”和轻子生成机制都是定性上很优美但定量上并不具有特定预言能力的理论图像,因此通过低能实验来检验这两种机制的有效性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如此,在不依赖模型相关的假设的前提下,我们依然可以对中微子的质量起源与宇宙的原初反物质消失之间的可能关联做出一些具有“考古学”依据的判断。
(1)中微子质量起源的“跷跷板”机制要求中微子具有马约拉纳属性,即在质量本征态下中微子的反粒子等于其自身。这一属性意味着轻子数破坏,会导致诸如无中微子的双贝塔衰变等轻子数不守恒过程的发生。基于著名的谢克特-瓦耶(Schechter-Valle)定理[12],只要在实验上发现了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的信号,那么不论该过程是否涉及其他新物理内容,都可以得出中微子具有马约拉纳属性的结论。目前的实验结果只是限定了某些核素可能发生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的半衰期,从而得到有效马约拉纳中微子质量项的上限[13]。下一代实验有望将探测半衰期的灵敏度提高一个数量级。
(2)在上述“跷跷板”机制中,轻的活性中微子与重的惰性中微子通过汤川相互作用而发生微弱的混合,后者导致活性中微子味混合矩阵不再是严格的幺正矩阵,其中微小的幺正性破坏效应有可能体现在诸如中微子振荡和带电轻子的味破坏衰变过程[14]。目前关于标准模型精确检验的实验数据和各种中微子振荡的实验数据已经限定了活性中微子味混合矩阵的幺正性破坏程度不会超过1%,未来的相关实验有望做出更严格的限制。
(3)为了解释宇宙的重子数与反重子数不对称,轻子生成机制要求重的惰性中微子在宇宙早期发生破坏CP对称性的衰变[15]。这种CP破坏效应有可能通过“跷跷板”机制体现在轻的活性中微子的振荡过程中,因此倘若在低能加速器中微子振荡实验中发现了CP破坏现象,也会增强人们对轻子生成机制的信心。目前日本的T2K中微子振荡实验已经在接近的置信度水平观测到了CP破坏的初步证据[16],未来的HyperK(日本)和DUNE(美国)等长基线中微子振荡实验有望令人信服地发现轻子CP不守恒。
在一些具体的“跷跷板”模型中,可以通过轻子生成机制建立中微子振荡中的CP破坏效应和宇宙的重子数密度与背景光子数密度之比之间的直接关联[17]。这类模型的细节通常依赖特殊的唯象学假设,更容易在实验上被证伪。但由于此类模型的任意性,实际上很难判断哪个模型更接近真实的物理现实。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其它类型的“跷跷板”机制通过引入其它重的自由度(如超越标准模型的新标量粒子或费米子)也可以解释活性中微子的质量起源与宇宙的原初反物质消失之谜,尽管它们的形式和内容可能显得更复杂一些。目前所有的理论尝试都还缺乏实验证据的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清楚中微子质量的起源问题是否一定与宇宙的重子数-反重子数不对称问题存在内在的关联。但无论如何,中微子的特殊性质为我们窥视物质结构和早期宇宙的奥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未来的实验和理论进展将有助于我们发现或接近上述基本问题的答案。
致谢 感谢与周顺研究员的有益讨论;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2075254、11775231、11835013)的资助。
作者 邢志忠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微子物理学的理论研究。
【推荐阅读文献】
[1] Minkowski P. Muon to electron and gamma at a rate of one out of one billion muon decays. Phys Lett B, 1977, 67: 421–428
[2] Fukugita M, Yanagida T. Baryogenesis with grand unification. Phys Lett B, 1986, 174: 45–47
[3] Majorana E. Teoria simmetrica dell’elettrone del positrone. Nuovo Cim, 14: 171–184
[4] Dirac P A M. The quantum theory of the electron. Proc R Soc Lond A, 1928, 117: 610–624
[5] Anderson C D. The apparent existence of easily deflectable positives. Science, 1932, 76: 238–239
[6] Dirac P. Theory of Electrons and Positrons. Nobel Lecture, 1933
[7] Sakharov A D. Violation of CP invariance, C asymmetry and baryon asymmetry of the universe. JETP Lett, 1967, 5: 24–27
[8] ‘t Hooft G. Symmetry breaking through Bell-Jackiw anomalies. Phys Rev Lett, 1976, 37: 8–11
[9] Particle Data Group. The review of particle physics. PTEP, 2020, 8: 083C01
[10] Kolb E W, Turner M S. The early universe. Front Phys, 1990, 69: 1–547
[11] Davidson S, Nardi E, Nir Y. Leptogenesis. Phys Rept, 2008, 466: 105–177
[12] Schechter J, Valle J W F. Neutrinoless double beta decay in SU(2)×U(1) theories. Phys Rev D, 1982, 25: 2951–2954
[13] Dolinski M J, Poon A W P, Rodejohann W. Neutrinoless double-beta decay: Status and prospects. Ann Rev Nucl Part Sci, 2019, 69: 291–251
[14] Antusch S, Biggio C, Fernandez-Martinez E, et al. Unitarity of the lepton mixing matrix. JHEP, 2006, 10: 084
[15] Xing Z Z, Zhou S. Neutrinos in particle physics, astronomy and cosmology.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11
[16] T2K Collaboration. Constraint on the matter-antimatter symmetry-violating phase in neutrino oscillations. Nature, 2020, 580: 339–344
[17] Xing Z Z, Zhang D. A direct link between unflavored leptogenesis and low-energy CP violation via the one-loop quantum corrections. JHEP, 2020, 04: 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