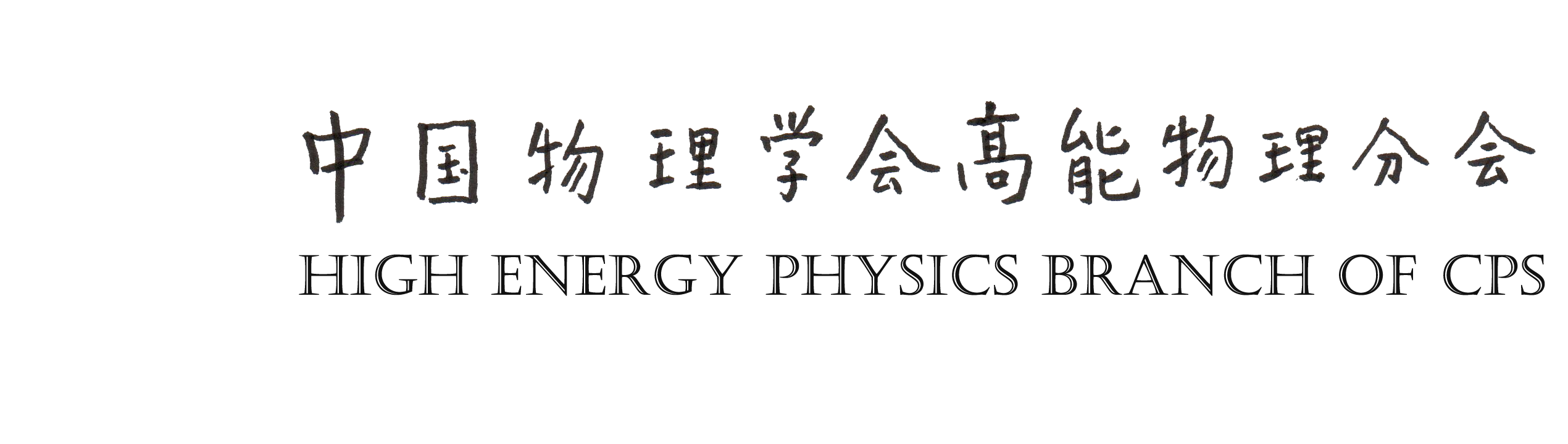一:宇宙大爆炸和夸克胶子等离子体
强相互作用力是自然界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之一,它将核子(质子与中子)束缚形成原子核并支配着自然界中90%以上的可见物质。量子色动力学(Quantum Chromodynamics, QCD)是描述强作用力的现代理论。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夸克与胶子,被强作用力禁闭在核子中,因此在自然界没有发现自由的夸克与胶子。物质在外界条件(如温度、压强等)改变时,会发生相变,比如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水,在不同条件下有固态(冰)、液态(水)、气态(水蒸气)三种不同的形态。水的固液气相变温度通常发生在零到几百摄氏度范围内,这是水分子在电磁相互作用层面上的相变现象。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把温度加热到万亿(≈ 1012)摄氏度—约为宇宙大爆炸几十微秒后的温度——物质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实际上,QCD理论预言,在这极高温度下,夸克与胶子将摆脱强作用力束缚,从核子中逃离(解禁闭),形成一种由自由夸克与胶子组成的新物质形态,即夸克-胶子等离子体(Quark-Gluon Plasma, QGP)。由于该新物质形态具有强耦合低粘滞流体的性质,又被称为“完美流体”(Perfect liquid),俗称“夸克汤”。由于QGP存在于宇宙早期,宇宙在膨胀冷却的过程中必然经历了从QGP到普通强子物质的转变。但在强作用层面上,自由夸克与胶子组成体系的相变机制还未能被人们所熟知,我们不知道物质在什么条件下如何从QGP相转换到普通的强子物质相。换句话说,我们对高温高密核物质相结构了解甚少。在致密天体(例如中子星)这种温度虽低但密度极大的强作用体系中,这一问题同样存在。因此研究核物质相结构(也被称为QCD相结构)有着重要科学意义,是当今国际核物理领域的前沿和热门课题。图1为宇宙大爆炸以及宇宙演化的示意图,图中标出了各个演化阶段的时间以及相应的物质存在状态。关于高温高密核物质相结构的研究,将对理解宇宙演化以及致密天体(如中子星等)的状态方程有重要意义,同时此研究被美国国家基础科学物理和天体物理理事会列为本世纪未解决的11大物理难题之一。

图 1: 宇宙大爆炸和演化示意图(图取自PDG LBNL 2015)
上世纪70年代,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先生率先提出用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即使用大型加速器将两束带电重离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发生碰撞)来形成并研究QGP。相对论重离子碰撞产生的能量将沉积在一个原子核大小的空间内,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出高温高密的物理环境。该环境将改变真空性质,从真空中激发出粒子并使夸克与胶子从强子中解除禁闭,形成由自由夸克与胶子组成QGP。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创造出的高温高密环境与宇宙大爆炸 (Big Bang) 初期产生的原初火球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也被称为小爆炸 (Little Bang), 它是目前人类在实验上创造并研究QGP性质及其相变的唯一方法。初始碰撞的核子在高能下碎裂,释放并激发出解禁闭的夸克与胶子,根据质能方程,越高的对撞能量激发出越多的粒子。碰撞产生的高温高密系统并非静态不变的,它由于存在的动能和压力梯度迅速膨胀冷却,当温度降低到临界温度 TC 以下时,夸克和胶子会经过复杂的反应重新结合成强子,发生从 QGP 相到强子物质相的相变。最后经过强子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稳定强子的衰变,得到在探测器上能够探测到的末态粒子。经过近20年的高能重离子碰撞实验研究,如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NL)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Relativistic Heavy Ion Collider, RHIC)和欧洲日内瓦的欧洲核子中心(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科学家们已经陆续发现了强耦合、低粘滞夸克胶子等离子体(sQGP)物质形态存在的多个简接证据:1)在CERN SPS核核碰撞中J/ψ粒子产额的压低[1];2)核核碰撞中奇异性产额的增强:在 QGP形成后,能量大于形成 ss¯ 夸克对的阈值,与 uu¯, dd¯ 夸克对一同大量产生,使奇异粒子如 K, Λ 产额提高[2];3)在 RHIC上观测到大横动量强子产额的压低、喷注淬火和由u,d,s,c夸克及反夸克组成的强子集体流的组分夸克数标度等[3][4]。

图2:QCD相图,纵坐标为温度T,横坐标为重子化学势µB。绿色区域为强子物质相,黄色区域为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相。黑色实线为一级相变边界。正方形框标示了可能的QCD临界点位置。红色实线为高能重离子碰撞的化学冻结线。红色点代表普通核物质的液气相变临界点。相图的顶部标出了不同重离子碰撞实验的相图覆盖范围。
二、核物质相结构和QCD相变临界点
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一个主要目标是研究QGP 相到强子物质相的相变,包括相变是如何进行的, 相变结构是什么以及是否存在一阶相变和临界点等。相结构可由相图描述,它揭示了物质的不同状态在温度、压强等宏观热力学条件改变下相互转化与共存的规律[5][6][7]。核物质相结构可由 QCD 相图表示。在图2中,横坐标代表重子化学势 µB,纵坐标代表温度 T,单位为兆电子伏特 (MeV) 。对于强相互作用物质(核物质)相变及其相结构,特别是高温高密情况下,我们知之甚少。这是因为QCD相图的标度(零重子密度下相转变温度)约为150-160 MeV[5][8][9],即万亿摄氏度,这样的极端高温在普通条件下很难达到,实验上只能通过相对论重离子碰撞产生的高温高密核物质来进行研究。另外,核物质相结构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由强作用力占主导的多粒子系统,属于非微扰问题,类似于研究强作用物质的凝聚态物理。QCD相图的高温低密区,与宇宙早期演化密切相关;低温高重子密度区与致密星体有关。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QGP相存在于高温高密区域,而强子物质相存在于 T 和 µB 较小的区域。QCD理论模型预言,强子物质相与QGP相之间是一阶相变,一阶相变边界的终结点被称为QCD相变临界点。相变临界点是物质状态方程的一个奇异点。1896 年 Andrews 观测到 CO2 气液相界面消失的现象,这是历史上首次观测到 CO2 位于压强 p = 73 atm, 温度T = 31°C 的临界点。临界点的特征性质是系统关联长度和密度涨落的发散。关联长度增大在实验上的一个重要的肉眼可观测现象是“临界乳光(Critical Opalescence)”,即气体处在临界点附近时,射入样品的光束的散射强度反比于光波波长,样品变得浑浊,呈现乳白色,本质上是因为样品中存在密度涨落的长程关联,其关联长度与入射光波波长可比拟,从而发生强烈的散射。与此原理类似的实验现象是在临界温度附近,晶体的 X 射线散射强度的异常增强。另外,铁磁体的磁化率(magnetic susceptibility) χ 被定义为磁化强度在外磁场改变下的变化率,即 χ = ∂M/∂H, χ 正比于关联函数的全空间积分,同时磁化率与可观测的热力学涨落密切相关。因此测量涨落与关联,可作为实验上间接寻找临界点信号的有效方法。
研究相变物理时,需要对引起相变的本质进行探索,我们先讨论相变过程有哪些一般性的变化。根据朗道相变理论,物质体系的相变对应体系对称性的改变[10]。例如在冰融化成水的过程中,晶体的长程有序结构被水分子的无序结构取代,对应晶体空间的 C6 对称性发生破缺 (冰晶属于六方晶系)。在铁磁相变理论中,铁磁性的产生与消失(铁磁相与顺磁相的相变)对应着铁磁体内旋转对称性的破缺和恢复:当旋转对称性破缺时,所有微观磁矩有统一固定的取向;当旋转对称性恢复时,铁磁体内微观磁矩随机分布,铁磁体呈现各向同性。在 BCS 理论中,超导体的超导态与非超导态之间的相转变,对应着 U (1) 规范对称性的破缺,与空间对称性对应晶体中位置与方向的变换不同,非超导态的规范对称性对应粒子相对相位的变换,关于 BCS 的相变对称性的理论在 1961 年由日本科学家Nambu在发表关于量子场论的 Nambu-Jona-Lasinio(NJL)模型时提出。回到 QCD 相变,其中与相变紧密相关的是手征对称性,手征对称性是 QCD 拉格朗日量具有的对称性,它表示左手自旋与右手自旋的夸克在规范变换下具有不变性,手征对称性的破缺程度可由手征凝聚 qq¯ 表示, qq¯ = 0 对应手征对称完全恢复的状态,因此 qq¯ 也是手征相变的序参量。其次,除了对称性的改变,相变还对应着体系自由度的改变。在冰融化成水的过程中,晶体的自由度被水分子的自由度取代;在 QCD 相变中,从低温到高温,强子自由度被“解禁闭”的夸克胶子自由度替代,介质中产生夸克胶子自由度的一个体现是色荷屏蔽作用的出现,正如一般“等离子体”的一个重要特征—电荷的自由迁移产生的电场对介质中的电荷产生了屏蔽作用。QGP 中存在色荷屏蔽作用的证据来自 CERN SPS 实验观测到 J/ψ 粒子产额的压低,这正是由于色荷屏蔽作用使得形成 J/ψ 的粲夸克与反粲夸克更难结合在一起,此外,长程色相互作用由于屏蔽作用趋于短程,减弱了色荷间的相互作用。虽然呈现色中性,但QGP中的色荷并未形成束缚态,这也是人们称其为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的原因之一。
三、QCD相变临界点的研究现状
- QCD相变临界点的理论研究
基于第一性原理研究QCD相变的一个重要工具是格点 QCD (Lattice QCD)[11]。通常情况下,微扰 QCD (perturbative QCD) 适用于耦合常数 αs 较小的情形,而QCD相变属于非微扰QCD问题,解析计算非常困难,需要用到格点QCD计算。计算结果表明,在 µB = 0 时QCD相变是一个平滑过渡(smooth crossover) [12],对于µB较大的情况,格点QCD计算会遇到所谓的
“费米子符号问题”而失效。因此人们转而构造基于QCD的有效模型来分析相变特征,其中包括由 Nambu等人提出的 NJL模型,多种模型计算表明高µB情况下是一阶相变。如果格点理论在µB =0的计算和有效模型的计算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便会想到,当µB 趋向于0,QCD一阶相变线必然会在某处终止。因此,1989 年日本科学家 浅川(Asakawa)和矢崎(Yazaki)就猜测一阶相变线的尽头存在被称为QCD 临界点的终止点。一个重要的前沿科学问题就是如何能在理论或实验上证实临界点的存在并确定其精确的位置。理论家们经过多年的尝试,运用如格点QCD中的重加权方法[13]、泰勒展开方法[14][15][16]和虚重子化学势方法[17]、泛函重整化群方法(FRG)[18][19]、NJL有效模型[20] [21][22]以及戴逊-施温格方程(DSE)[23][24]等,试图通过理论计算得到QCD临界点的位置,但是不同的理论模型和方法给出的结论差别较大,甚至其位置存在与否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科学家们期望能够从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实验中寻找QCD临界点的信号,并确定其在QCD相图中的位置。但从实验上寻找 QCD 临界点仍然存在较多困难,对于极高温度、密度和极小空间、时间尺度上的QCD 相变,我们很难进行直接观测,只能通过间接方式去测量相变的信号。

标为重子化学势。右:当系统穿过临界区域,守恒荷分布的峰度乘以方差 κσ2
 随着碰撞能量的改变,围绕泊松分布基线显示出的非单调振荡行为[25]。
随着碰撞能量的改变,围绕泊松分布基线显示出的非单调振荡行为[25]。理论学家们20多年前提出了将重离子碰撞实验中末态带电 π 介子多重数逐事件涨落作为寻找QCD 临界点信号的观测量。在 2000 年,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浅川(Asakawa)等提出将强相互作用中的守恒量,如净电荷数,净重子数和净奇异数的逐事件涨落作为观测,这是由于粒子数的逐事件涨落 < (δN )2 > 与物质中的热力学感应率 (susceptibility) χ密切相关。与磁化率类似,χ = ∂(P/T 4)/∂µB,表示系统无量纲压强 P/T 4 随参数 µB 的变化率。但遗憾的是,在这些观测量中,相对论重离子碰撞实验一直没有探测到理论预言的QCD临界点的信号。2009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UIC)的Misha Stephanov教授首次提出在重离子碰撞实验中测量守恒荷(如重子数、奇异数、电荷数) 分布的高阶矩(方差(σ2
 )、偏度(S)、峰度(κ
)、偏度(S)、峰度(κ ))来寻找QCD临界点[25]。这是因为在临界点附近关联长度发散,守恒荷分布的高阶累积矩对关联长度更敏感,如四阶累积矩正比于关联长度的七次方。另外,临界点附近,非高斯涨落会增强,而高阶累积矩对非高斯涨落非常敏感。巧妙地选择这些观测量不仅是因为它们与临界涨落密切关联,也因为它们是实验中的直接观测量,各阶累积矩的比值和理论计算的高阶磁化率可以直接联系起来,比如守恒荷分布的峰度乘以方差κσ2
))来寻找QCD临界点[25]。这是因为在临界点附近关联长度发散,守恒荷分布的高阶累积矩对关联长度更敏感,如四阶累积矩正比于关联长度的七次方。另外,临界点附近,非高斯涨落会增强,而高阶累积矩对非高斯涨落非常敏感。巧妙地选择这些观测量不仅是因为它们与临界涨落密切关联,也因为它们是实验中的直接观测量,各阶累积矩的比值和理论计算的高阶磁化率可以直接联系起来,比如守恒荷分布的峰度乘以方差κσ2 和四阶(χ4
和四阶(χ4 )、二阶(χ2
)、二阶(χ2 )热力学感应率之比密切相关(κσ2
)热力学感应率之比密切相关(κσ2 =χ4/χ2
=χ4/χ2 ),这样就架起了联系理论和实验的桥梁。当改变重离子碰撞能量,碰撞中形成的高温高密核物质的化学冻结温度和重子化学势也将发生改变(能量越低,温度越低,重子化学势越大),并穿过临界区域(图3左)。此时,守恒荷涨落将受到临界涨落的影响。系统的化学冻结条件(T,µB)到QCD相图中临界点位置的距离逐渐减小然后增大,关联长度会先增大后减小。因此在重离子碰撞能量扫描中,当临界区域被穿过的时候,临界点的一个特征信号就是守恒荷分布的高阶矩对能量的非单调依赖(图3右)。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模型计算是基于达到热平衡且有无限大体积的静态系统,这和重离子碰撞中快速膨胀的非平衡和有限体积效应的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差别。因此构建含临界点物理的重离子碰撞动力学模型是理论家们研究的热点问题[26]。
),这样就架起了联系理论和实验的桥梁。当改变重离子碰撞能量,碰撞中形成的高温高密核物质的化学冻结温度和重子化学势也将发生改变(能量越低,温度越低,重子化学势越大),并穿过临界区域(图3左)。此时,守恒荷涨落将受到临界涨落的影响。系统的化学冻结条件(T,µB)到QCD相图中临界点位置的距离逐渐减小然后增大,关联长度会先增大后减小。因此在重离子碰撞能量扫描中,当临界区域被穿过的时候,临界点的一个特征信号就是守恒荷分布的高阶矩对能量的非单调依赖(图3右)。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模型计算是基于达到热平衡且有无限大体积的静态系统,这和重离子碰撞中快速膨胀的非平衡和有限体积效应的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差别。因此构建含临界点物理的重离子碰撞动力学模型是理论家们研究的热点问题[26]。 

图 4: (左)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 (RHIC) 和 (右) STAR探测器。
- QCD相变临界点的实验研究进展
QCD临界点的实验确认将是探索核物质相结构的里程碑,具有重要科学意义。为了在这一具有潜在重大发现的研究方向上占据领先地位、取得突破,各个国家纷纷建造大型粒子探测器、开展重离子碰撞实验(包括:美国RHIC-STAR能量扫描实验,德国FAIR-CBM实验、俄罗斯 NICA-MPD实验、日本J-PARC实验以及中国兰州CSR外靶CEE实验),其主要物理目标就是研究高温高密核物质相图结构、寻找QCD相变临界点。RHIC,即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 (图4左), 位于美国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RHIC 的主体是周长 3.8 公里的两个加速圆环,其中一束束流按顺时针方向进入“蓝环”,另一束束流按逆时针方向进入“黄环”,在各自的圆环上被加速,并可以在圆环的 4 个交汇点碰撞。人们在这些碰撞点上建造了4台复杂而精密的粒子探测器。STAR (Solenoidal Tracker At RHIC,即螺旋管径迹探测器) ,位于RHIC六点钟方向,是RHIC上唯一一个目前在运行并专门被用于研究高温高密核物质性质以及QCD相变相关物理的探测器(图4右)。STAR 探测器具有较大中心快度区域的全方位角接收度(|η
 |<1,2π
|<1,2π ), 具有多径迹事件重建能力,能够直接提供大动量范围(0.2~30 GeV/c)的带电粒子信息,是由不同探测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大型探测器复合装置。RHIC从2010-2014年进行了第一阶段重离子碰撞能量扫描(Beam Energy Scan-I),其主要物理目标就是通过改变金核金核的对撞能量 (相当于改变系统的温度T和重子化学势 µB),来扫描QCD相图,并利用敏感的实验观测量来寻找QCD相变临界点信号。RHIC 能量扫描实验中,两束被剥离核外电子的金原子核 (原子序数 79) 在电场中加速到极高能量后发生对撞,每核子对的质心能量可以达到 7.7∼200 GeV,对应的重子化学势范围约为 420∼20 MeV,这覆盖了较宽的QCD相图区域,使得从实验上寻找QCD临界点成为可能。
), 具有多径迹事件重建能力,能够直接提供大动量范围(0.2~30 GeV/c)的带电粒子信息,是由不同探测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大型探测器复合装置。RHIC从2010-2014年进行了第一阶段重离子碰撞能量扫描(Beam Energy Scan-I),其主要物理目标就是通过改变金核金核的对撞能量 (相当于改变系统的温度T和重子化学势 µB),来扫描QCD相图,并利用敏感的实验观测量来寻找QCD相变临界点信号。RHIC 能量扫描实验中,两束被剥离核外电子的金原子核 (原子序数 79) 在电场中加速到极高能量后发生对撞,每核子对的质心能量可以达到 7.7∼200 GeV,对应的重子化学势范围约为 420∼20 MeV,这覆盖了较宽的QCD相图区域,使得从实验上寻找QCD临界点成为可能。

 的能量依赖。右下图展示了PHENIX实验测得的净电荷κσ2
的能量依赖。右下图展示了PHENIX实验测得的净电荷κσ2 结果,误差棒和方框分别代表统计误差和系统误差。
结果,误差棒和方框分别代表统计误差和系统误差。STAR实验从2010-2017年采集了第一阶段金-金碰撞能量扫描数据(质心能量分别为: 7.7,11.5,14.5,19.6,27,39, 54.4, 62.4,200 GeV) ,并完成了净质子[27][28][29][30][31]、净电荷[32]以及净K介子数分布的高阶矩分析[33]。图5展示了STAR实验测量的净质子、净电荷和净K介子数分布的四阶矩(峰度乘以方差,κσ2
 )以及PHENIX实验净电荷测量结果。STAR实验测量的净电荷以及净K介子数四阶涨落由于统计误差较大,没有显示出明显的非单调能量依赖,需要进一步提高事件量。最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结果是,STAR首次在金-金中心碰撞中观察到了净质子数四阶涨落κσ2
)以及PHENIX实验净电荷测量结果。STAR实验测量的净电荷以及净K介子数四阶涨落由于统计误差较大,没有显示出明显的非单调能量依赖,需要进一步提高事件量。最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结果是,STAR首次在金-金中心碰撞中观察到了净质子数四阶涨落κσ2 对碰撞能量的非单调依赖[27] (显著性为3.1倍标准偏差),即能量在39 GeV以上,接近于1,在19.6和27 GeV显著低于1,而在更低能量大于1 (图5左上)。这个非单调的行为可能暗示了热密核物质系统穿过临界区域,从而接收到临界涨落正的和负的贡献[25]。但在碰撞能量20 GeV以下,净质子数的测量统计误差仍较大。相较于STAR实验,PHENIX实验测量的净电荷结果显示出较小统计误差,这是由于其探测器接受度比STAR实验小很多。为了缩小实验统计误差,BNL计划升级RHIC加速器的电子冷却系统以及STAR实验相关子探测器,并在2019-2021年进行第二阶段能量扫描(集中扫描20 GeV以下能量点),进一步缩小统计误差。另一方面,守恒荷涨落可能受到与临界点无关的非临界背景涨落的干扰。这些非临界效应的贡献包括如重子数守恒、重子纵向输运,非平衡效应,体积涨落、末态强子衰变以及强子散射。这些背景源可以用理论模型来进行研究[34][35][36][37]。在这些实验测量中,中国STAR实验研究团队做出了重要贡献,完成了第一阶段RHIC能量扫描中净质子、净电荷以及净K介子数涨落的实验测量。同时在高阶矩数据分析过程中,研究团队克服困难,解决了遇到的一系列数据分析难题,逐步发展出一套有效提取信号的方法,包括压低体积涨落效应[38]、消除自关联本底[39]、修正探测效率以及精确计算统计误差[40][41][42],这些数据分析方法对获得精确实验结果至关重要。
对碰撞能量的非单调依赖[27] (显著性为3.1倍标准偏差),即能量在39 GeV以上,接近于1,在19.6和27 GeV显著低于1,而在更低能量大于1 (图5左上)。这个非单调的行为可能暗示了热密核物质系统穿过临界区域,从而接收到临界涨落正的和负的贡献[25]。但在碰撞能量20 GeV以下,净质子数的测量统计误差仍较大。相较于STAR实验,PHENIX实验测量的净电荷结果显示出较小统计误差,这是由于其探测器接受度比STAR实验小很多。为了缩小实验统计误差,BNL计划升级RHIC加速器的电子冷却系统以及STAR实验相关子探测器,并在2019-2021年进行第二阶段能量扫描(集中扫描20 GeV以下能量点),进一步缩小统计误差。另一方面,守恒荷涨落可能受到与临界点无关的非临界背景涨落的干扰。这些非临界效应的贡献包括如重子数守恒、重子纵向输运,非平衡效应,体积涨落、末态强子衰变以及强子散射。这些背景源可以用理论模型来进行研究[34][35][36][37]。在这些实验测量中,中国STAR实验研究团队做出了重要贡献,完成了第一阶段RHIC能量扫描中净质子、净电荷以及净K介子数涨落的实验测量。同时在高阶矩数据分析过程中,研究团队克服困难,解决了遇到的一系列数据分析难题,逐步发展出一套有效提取信号的方法,包括压低体积涨落效应[38]、消除自关联本底[39]、修正探测效率以及精确计算统计误差[40][41][42],这些数据分析方法对获得精确实验结果至关重要。
图 6:(左)轻核(d, t)组成以及密度涨落示意图。(右) RHIC第一阶段能量扫描金核金核碰撞中轻核产
额比Nt*Np/Nd2 对碰撞能量的依赖[48]。
除了在STAR实验中开展守恒荷分布的高阶矩测量,近几年来中国STAR研究团队也尝试测量了其它对QCD临界点敏感的观测量。核子合并模型预言,氘(d)、氚(t)、氦(He)等轻核是由核子合并而成,它们的产额会受到临界点附近较强的核子密度涨落影响(图6左)。当系统穿过临界区的时候,核子数密度涨落的增大会导致轻核(如氘、氚、氦等)的产额受到影响,且轻核产额的比值(Nt*Np/Nd2
 )与中子数密度涨落直接相关。因此轻核的产额比可以作为寻找QCD临界点的敏感观测量[43][44][45][46],为研究QCD相变和临界点提供了又一重要的工具。STAR实验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能量扫描金核金核碰撞中氘核(deuteron)[47]和氚核(triton)[48]横动量谱以及产额的测量,可计算得到氘核(deuteron)、氚核(triton)以及质子的产额比值Nt*Np/Nd2
)与中子数密度涨落直接相关。因此轻核的产额比可以作为寻找QCD临界点的敏感观测量[43][44][45][46],为研究QCD相变和临界点提供了又一重要的工具。STAR实验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能量扫描金核金核碰撞中氘核(deuteron)[47]和氚核(triton)[48]横动量谱以及产额的测量,可计算得到氘核(deuteron)、氚核(triton)以及质子的产额比值Nt*Np/Nd2 。从图6右可以看到,产额比随着能量的降低显著上升,在20-27 GeV附近出现一个峰的结构,能量进一步降低时,又开始下降,整体显示出对碰撞能量的非单调依赖行为。我们发现在低能量区域,STAR实验结果与基于NA49实验合作组铅核铅核的轻核实验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一致[43][49]。基于简单的末态核子合并,不包含临界点物理的输运模型JAM被用来计算了轻核产额比,发现结果在误差范围内没有能量依赖,JAM模型结果与200 GeV实验测量接近,不能描述实验观测到的非单调能量依赖行为[50]。实验测量到的非单调能量依赖是否与临界点或一阶相变有关,有待进一步的实验和理论研究。该实验测量结果为研究不同能量下轻核产生机制以及将来QCD临界点的寻找提供了重要实验依据。
。从图6右可以看到,产额比随着能量的降低显著上升,在20-27 GeV附近出现一个峰的结构,能量进一步降低时,又开始下降,整体显示出对碰撞能量的非单调依赖行为。我们发现在低能量区域,STAR实验结果与基于NA49实验合作组铅核铅核的轻核实验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一致[43][49]。基于简单的末态核子合并,不包含临界点物理的输运模型JAM被用来计算了轻核产额比,发现结果在误差范围内没有能量依赖,JAM模型结果与200 GeV实验测量接近,不能描述实验观测到的非单调能量依赖行为[50]。实验测量到的非单调能量依赖是否与临界点或一阶相变有关,有待进一步的实验和理论研究。该实验测量结果为研究不同能量下轻核产生机制以及将来QCD临界点的寻找提供了重要实验依据。

图 7: STAR探测器3D图,图中标出了在第二阶段能量扫描(2019-2021)中升级的子探测器,
分别为iTPC, EPD以及eTOF。四、RHIC第二阶段能量扫描及未来高重子密度区重离子碰撞实验
RHIC第一阶段重离子碰撞能量扫描实验以及相关实验测量结果扩展了我们对核物质相图的认识,但是相关重要观测量的误差仍然较大,不足以给出QCD临界点是否存在的明确结论。例如我们在STAR第一阶段金金碰撞能量扫描实验中测量了净质子数的涨落,观察到明显的非单调能量依赖(图8左),这与理论预言当系统穿过临界区时,QCD临界区域引起的粒子数四阶涨落能量依赖信号符合。但是由于事件量的限制,20 GeV以下的测量结果的统计误差仍较大。为了缩小误差,进一步确认在第一阶段能量扫描中观测到的各种重要实验测量结果,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NL)升级了RHIC加速器束流冷却系统,可提供低能量下较高的束流亮度,从而提高实验数据量。从2019到2021年,RHIC第二阶段能量扫描[51]将集中扫描20 GeV以下的几个质心能量点(19.6、14.5、11.5、9.2、7.7 GeV)。为了扩展粒子探测效率、粒子鉴别能力以及探测器接受度(见图7),STAR实验对时间投影室TPC的内径迹重建部分(inner)完成了升级(iTPC),并建造了新的事件平面探测器(EPD)以及端盖时间飞行探测器(ETOF),它们已经在2019年被成功用于实验数据采集。当前STAR实验已经采集了第二阶段能量扫描的4个对撞能量点,质心能量分别为: 19.6, 14.5,11.5和 9.2 GeV。采集的事件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数据刻度以及物理分析也正在有序进行。

在RHIC第一阶段能量扫描的金金对心碰撞中,STAR实验观测到了净质子数分布的四阶矩κσ2
 和轻核产额比Nt*Np/Nd2
和轻核产额比Nt*Np/Nd2 的非单调能量依赖,分别在20 GeV附近出现了一个极小值和极大值。尽管两个观测量测量的是不同阶次的涨落,但是测量结果和包含临界点物理的模型预言结果一致,可能暗示了碰撞产生的热密系统穿过了临界区,并受到临界涨落的影响。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19.6 GeV (μB=205
的非单调能量依赖,分别在20 GeV附近出现了一个极小值和极大值。尽管两个观测量测量的是不同阶次的涨落,但是测量结果和包含临界点物理的模型预言结果一致,可能暗示了碰撞产生的热密系统穿过了临界区,并受到临界涨落的影响。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19.6 GeV (μB=205 MeV) 和 14.5 GeV(μB=266
MeV) 和 14.5 GeV(μB=266 MeV),净质子数分布的四阶矩和轻核产额比均显示出一个较大变化。不能排除自然界恰好将临界点放在这两个能量的热力学条件之间。因此我们建议有必要对19.6和14.5 GeV之间做一个更细致的扫描。在RHIC第二阶段能量扫描加一个新的能量点,16.7 GeV(μB=235
MeV),净质子数分布的四阶矩和轻核产额比均显示出一个较大变化。不能排除自然界恰好将临界点放在这两个能量的热力学条件之间。因此我们建议有必要对19.6和14.5 GeV之间做一个更细致的扫描。在RHIC第二阶段能量扫描加一个新的能量点,16.7 GeV(μB=235 MeV),该能量的化学冻结重子化学势恰好在19.6 和 14.5 GeV之间,并分别与这两个能量的重子化学势等间距。理论预言,能量继续降低,将使得系统远离临界区域,这样净质子数四阶涨落将回落到统计涨落的泊松基线值1,并形成一个峰的结构(图3右)。德国GSI的HADES实验已经测量了金金打靶碰撞0-10%中心度,质心能量2.4 GeV的质子数四阶涨落,发现值在0附近,但是误差很大(图8左)[52]。因此在质心碰撞能量2-8 GeV之间测量守恒荷涨落,并验证实验结果是否在低能量时回落到泊松
MeV),该能量的化学冻结重子化学势恰好在19.6 和 14.5 GeV之间,并分别与这两个能量的重子化学势等间距。理论预言,能量继续降低,将使得系统远离临界区域,这样净质子数四阶涨落将回落到统计涨落的泊松基线值1,并形成一个峰的结构(图3右)。德国GSI的HADES实验已经测量了金金打靶碰撞0-10%中心度,质心能量2.4 GeV的质子数四阶涨落,发现值在0附近,但是误差很大(图8左)[52]。因此在质心碰撞能量2-8 GeV之间测量守恒荷涨落,并验证实验结果是否在低能量时回落到泊松涨落基线,并形成一个峰的结构,将是确认QCD临界点信号关键一步。

 GeV,蓝色实心方框为NICA的对撞能量点:4<sNN<11
GeV,蓝色实心方框为NICA的对撞能量点:4<sNN<11 GeV。固定靶实验的质心能量点包括:STAR FXT:3<sNN<7.7
GeV。固定靶实验的质心能量点包括:STAR FXT:3<sNN<7.7 GeV (红色实心圆圈), HADES: 2<sNN<3
GeV (红色实心圆圈), HADES: 2<sNN<3 GeV (菱形), HIAF: 2<sNN<4.2
GeV (菱形), HIAF: 2<sNN<4.2 GeV (红色空心正三角), FAIR/CBM : 2<sNN<5
GeV (红色空心正三角), FAIR/CBM : 2<sNN<5 GeV (红色实心倒三角)。
GeV (红色实心倒三角)。STAR实验合作组在2011年论证了将STAR探测器运行在固定靶模式的可行性。即在时间投影室(TPC)一端,距离中心210cm处放置一个1毫米厚的金箔作为固定靶,并用单向束流去轰击该靶。因此在RHIC第二阶段能量扫描中(2019-2021),STAR实验也计划采集更多低能量点的固定靶实验数据,包括以下质心能量点:7.7、7.2、6.2、 5.2、4.5、4、3.5和3 GeV。因此,除了分析第二阶段能量扫描中金核金核对撞的实验数据,STAR实验将基于将来采集的固定靶实验数据开展寻找QCD临界点信号的实验测量。另一方面,理论预言守恒荷越高阶涨落对QCD相变越敏感。在相变温度附近,净重子数六阶和八阶涨落相比四阶涨落更敏感且起伏更大,六阶和八阶涨落将变为负值。然而实验上相对于低阶,高阶更难精确测量,需要更多的事件量。STAR实验已经对2010和2011年采集的200 GeV金金对撞实验数据以及2017年采集完成的54.4 GeV实验数据完成了净质子分布的六阶矩测量。结果显示54.4 GeV和200 GeV金金对撞中,两个能量的边缘碰撞结果一致。但在0-40%金金中心碰撞中54.4 GeV的测量结果为正,而200 GeV为负值[53]。该负值与格点QCD计算结果符合[54],可能暗示碰撞产生的高温低重子密度核物质经历了QCD相变。但是目前实验统计误差较大且为较宽碰撞中心度(0-40%)。将来的固定靶实验,由于有较大的束流亮度,这使得我们有足够的统计量来对净质子数分布的六阶甚至八阶进行精确测量。为了在探索高重子密度区核物质相结构、寻找QCD相变临界点这一具有重大发现潜力的研究方向上占据领先地位、取得突破,世界各大科技强国纷纷建造大型加速器和粒子探测器、开展重离子碰撞实验(见图9),其中包括德国FAIR的压缩重子 (Compressed Baryonic Matter, CBM) 实验[55]、欧洲核子中心(CERN) SPS/NA61实验[56]、日本J-PARC实验[57]、俄罗斯杜布纳(Dubuna)联合核子研究所NICA Multi-Purpose Detector (MPD)重离子对撞实验[58]、中科院近代物理所HIRFL-CSR External-target (CEE) 外靶实验[59]。这些未来的大型国际合作实验将对探索高重子密度区核物质相结构、寻找QCD相变临界点起到重要作用,并有望在该研究方向上取得突破。国内科研单位积极加入这些实验并参与探测器研制和建造。我国十二五大科学装置强流离子加速器(HIAF,坐落于广东惠州,预期2025年建成)也将开展相关实验研究[60]。围绕该关键物理问题的研究将推动我国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与投入,为我国高科技技术发展及人才培养提供良好平台。
结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受限于我们视野能够到达的界限,宇宙大爆炸已经过去137亿年,但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我们再一次深入到这一极端高能与极端微小的领域,一睹自然规律令人惊叹与着迷的一面。相对论重离子碰撞的科研领域与天文学、凝聚态物理乃至工程技术密切相关,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基石之一。因此我们热忱地欢迎读者继续关注这一领域的进展。
致谢 本文由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 (编号: 2015CB856900)、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8YFE02052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编号: 11890711、11927901、11575069、11828501、11861131009)资助。